“我”因无事可做,乘着北上列车去往加格达奇。车上遇到一位拉手风琴的大叔,给我讲了一段冗长而繁复的爱情故事:男人叫甘伯,女人叫宋爰(音援,有“何处”之意)。这一男一女的生死纠缠跨越时间与空间,既发生在古代,也发生在未来,既发生在中国,也发生在西洋。故事里有国王、巴黎、革命、宋代、官府衙门、时尚杂志、嘻哈音乐等等,要素繁多,场面锦簇,远比车窗外北方的风景更加迷人。
《甘伯记》不是一部典型的穿越小说。穿越故事的时空设置相互独立,并因其独立性不得不穿越。而此书在一个时空内就将多种要素同时融合,丰富又有些无从下口。故事看到最后,埋下了无数草蛇灰线。
予人大惊奇者,或大智慧,或大野心。如果读不懂一部作品,就先看作者经历,文字都是人的命运投射。作者张广天生于六十年代,驰骋先锋艺术领域数十年载从音乐到诗歌,从戏剧到小说,见证了一个社会从理想主义到流量殖民的衰落,一代代人从热血到冷漠的献祭。
有人或忍看或任看朋辈成新鬼,但有人不忍,要呐喊,要抗争,几近声嘶力竭乃至显挑衅相,虽结局不可撼但已尽力,至少于自我内心稍稍可安,不枉红尘一场。
或可言本书的技法本身也是种隐喻:看似繁华但过分丰腴者,亦露光怪陆离相。恰如当世每日面对五光十色的信息席卷,琳琅满目如进入六道大观园,古今中外痴男怨女皆融于方寸一屏,如先知掌着水晶球,窥透万千命运,但自洽自得后,心后亦是虚空万丈。
人类命运是一部失败史。武断点说,好的故事也都以求不得收尾,爱情更是如此。不信你去问贾宝玉、于连、杜拉斯、乔峰、王琦瑶;《倾城之恋》本质也是悲剧,白流苏与范柳原重温旧梦,但搭上了一座城池,只是故事收尾在一个高潮的结点,但作者没有继续言明的,是未来的一地鸡毛。
本书也是一样,如作者开篇言:“得不着爱情的痛苦已经写得太多,如今,我要写一个因得着爱情而痛苦的事。”因求得了而徒增爱别离与怨憎会,是更大的悲剧。
爱情是,其他也是,整个人类史都是。
我不愿擅用“魔幻现实”一词,我更倾向将此书归为诗歌的小说化,作者也不止一次在书中提到法语与波德莱尔:“他还是喜欢讲波德莱尔,只是这年岁重温《恶之花》,心境全然不同。以往他所见之恶,都是社会的和制度的;今日他体会到的恶,竟是发乎自身来自性情的。”
参考作者之前已出版的叙事长诗《玉孤志》中对波德莱尔的借鉴与引用,亦可断言这是他的文学师承:以妖艳书荒芜,以多彩言阴暗,以欲望展丑陋,以享乐喻沉思。
在如今这长篇叙事没落的小说末法时代,作者拗有先锋派的行文风格,于当下维度难以定论:到底是一个康波周期的挽歌?还是某种中兴乃至又开辟出某条新路径?
时代已不再拥有耐心,但如果少数读者仍秉承后知后觉的质朴,在若干年后回翻此书,或许能有更新的视角与更熨帖的概念。
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序言中说:“一本书是一个空间,读者在它里面走动,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,但在某一个时刻,找到一个出口,或许是多个出口,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。”
读《甘伯记》也有此种乱花迷人眼而后一落白寻轻的体验。“在地狱里寻找非地域的人和物,学会辨别他们,使他们存在下去,赋予他们空间。”
愿我们都有此等宽容力与幸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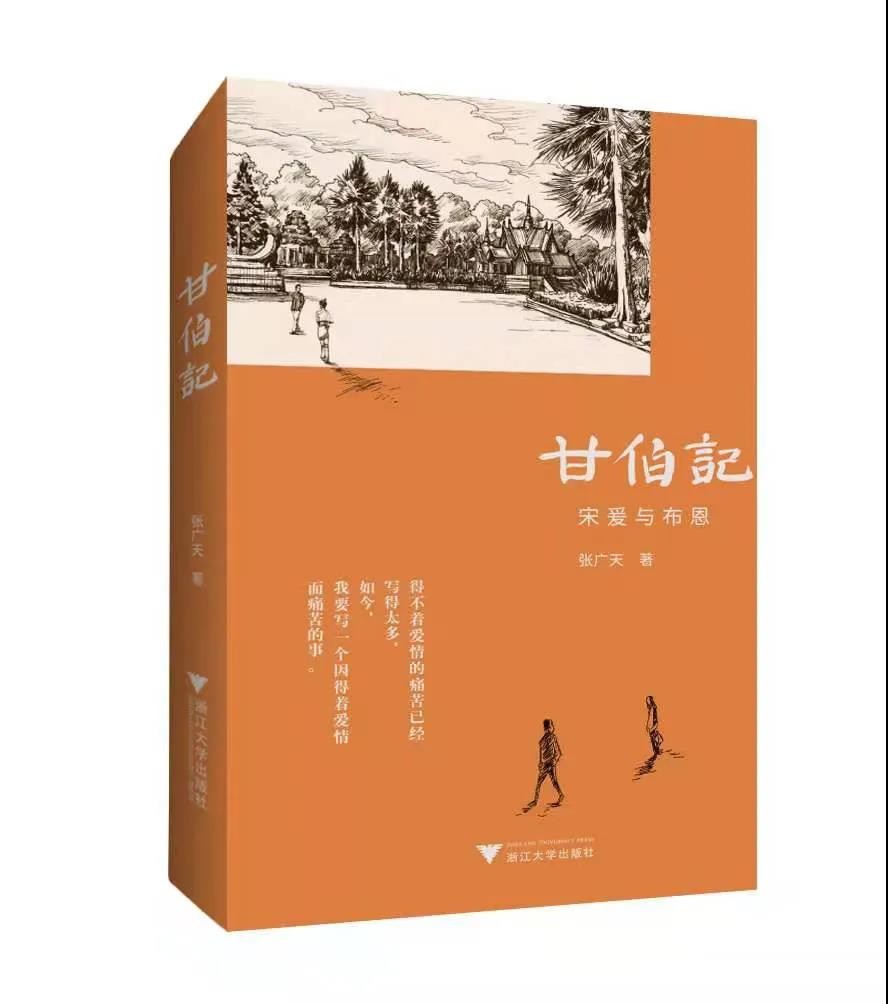
郑重声明: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,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,与本站立场无关。仅供读者参考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
















